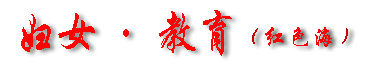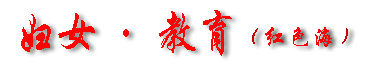|
|
| | |
| | 让神握住你的手
| | | | 《云南映象》以杨丽萍的《雀之灵》结尾,一支洁白的羽毛缓缓飘落。万籁俱寂中,生命自有任何语言也无法述说的丰富博大与庄严。良久,人们含着泪水离开。民族舞蹈或许从此找到了从民间走向更大舞台的出路,或许也是一种缺失的开始……
让神握住你的手
60面鼓的鼓风鼓韵将人们从现代社会拉到了混沌之初山野之颠,巨大的鼓声似风又似野火,仿佛人的魂魄铸进鼓里,其中狂欢女子的擂鼓也让人感受到来自红土地蓬勃的生命力。一大群拉车的放牛的从云南民间来的人一起跳啊跳啊,黝黑的皮肤粗犷的线条,汪洋姿肆的动作, 没有在山野民间群舞时的尘土飞扬, 只有一种真正的酒神似的狂欢。这是杨丽萍最新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的序幕. 杨丽萍在沉寂两年之后奉献给人们的一台汇集了云南十几个民族舞的大联欢。细细数来,这位孔雀公主已经成名18载了,而她真正的艺术生命则显然远远不止18年。
童年与舞蹈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杨丽萍就出生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的一个小村寨里。
苍山,又名点苍山,在风和日丽的阳春三月,点苍山顶显得晶莹娴静。洱海是一个风光明媚的高原湖泊,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泛舟洱海,干净透明的海面宛如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悠远的感受。
而她是一个在小村寨光着脚丫到处拾麦穗的乡下小姑娘,家里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取暖用柴火。伸手就可以摘到桃子吃,出门就可以见到一条清澈的河水,可以在那儿洗菜、打水。在坡上、在河边,放牛、放马,在她的身边都是盛开的向日葵,还有倒映在水里的身影。闲时躺在河边,抬头看流云无穷的变化,树影的婆娑,自然的点点滴滴充满了整个童年。在她童年世界里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天地可以交融,阴阳可以协调。大自然是最美、最真实、最深刻的体现。 山会赋予你固执也是执著, 水会带给你变通也是柔情。临水起舞是孔雀展示美丽形态的方式也是云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杨丽萍从小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云南人在插秧节上就会有仪式,祈求上天使来年丰收。像女孩子出嫁,白族人13岁过门,就是定亲,大家要跳舞,祝福新人。出嫁的时候爱唱出嫁歌或者哭嫁歌,凡是表达对自然信仰或和繁衍生殖有关系的事情就要跳舞。
小的时候, 爷爷死了,奶奶从早唱歌唱到晚,奶奶把爷爷这一生、她对他的思念哀悼,通过歌这种方式哭诉出来。小时候奶奶还告诉她,跳舞的时候如果神没有握住你的手,你就跳不好。在以后的几十年人生岁月里她一直让神紧握着自己的手。在杨丽萍的童年记忆里,大都与贫穷有关,但却从来没有阴影, “其实我从生下来到现在就没有一天不快乐,没有一天不幸福!”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这样淳朴空灵的环境成长起来的人, 天生就有对于艺术的敏感性, 天生就有对于生活通达的智慧,杨丽萍日后的艺术与生活也证实了这一点。
飞腾与宁静
1971年,13岁的她从村寨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 开始职业舞蹈生涯。20世纪80年代,她来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她奇怪民族舞竟然要学芭蕾,跳舞要绷着腿,演西施的时候腿要举到头顶,冲着观众张开腿,或者做一些不伦不类的芭蕾动作。于是她根本就不按常规动作练习。
1986年,作为一名不听话的学生,她创作了独舞《雀之灵》参加舞蹈比赛。每月工资才100多块钱,她卖掉了心爱的手表,用借来的700元钱买了孔雀裙,配乐需要1000元,因为没有钱,没有及时地把音乐和录像带做出来。那时候不是亲自去表演,而是把录像带送到评委会先去参评。等到她把钱一点点凑齐了,已过了比赛预选时间。她至今还记得当时她拿到那个录像带的时候正下着瓢泼大雨,骑着自行车把它送去,可人家说已经截止,不收了。后来是值班的一个老师说,这样吧,你先把它留下来,等到评委休息或者吃饭的时候,我想办法把它放出来,让他们看。
后来,她突然接到了参加决赛的通知。《雀之灵》在决赛中得了一等奖。得奖的时候她没有哭,比较平和,28年的人生岁月她一直坚信所有的事都是应该的或者不应该的,不用太多的去强求。
成名后的18年里, 她虽然出现在春节晚会,又屡次到国外巡演, 得了国际奖和政府奖, 也得了观众投票的奖,但她的身影只会出现在舞台上。她的舞蹈也许已经走到别人看来的巅峰,也许在等待一次突破,也许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使命与超越
她曾经一度想过离开舞台,但是把民族舞蹈传承下去的使命感却在驱使着她,也许她30年的职业舞蹈生涯都在等待一次超越,40年的人生岁月都在想着找到一种方式实现她心中想到的东西。1997年,杨丽萍随派格太合环球传媒《为中国喝彩》晚会节目去过4个国家,每到一处,杨丽萍哪里都不逛,只是不停地看当地的舞蹈演出,然后回房间琢磨,看了想,想完再看。她用一年多的时间在云南民间采风,把云南本土十几个民族的舞蹈还原在一个舞蹈集里,用了四分之三从云南乡间拉来的乡亲做演员,于是有了2003年的《云南映象》。
杨丽萍在《云南映象》里有四段舞蹈,其中三段舞蹈傣族元素比较多,有一段是佤族的舞蹈。舞蹈中她在手上或者身上画上图案,来象征一些万物灵性的感觉和意识。还把眼睛画在手上,通过手去观察到另外不同的东西。从来老人们就教她们你不能用正常的眼睛去看,你要用心灵甚至另外一种眼睛去观察,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天地可以交合,所以你要用精神的眼睛或者心灵的眼睛去观察。
“林”这一场,舞台上只有屏幕,没有演员,演员的人影和热带雨林的光影在屏幕上虚虚实实地交错,像五彩的抽象画也像云南工笔重彩画。它使舞者变成了林中的精灵,与自然融为一体。云南的少数民族在劳作之余喜欢在广场上跳集体舞,他们称为‘打歌’或‘跳锅庄’。大量使用的可以移动升降转换的装置突破了以往舞台艺术的均衡布局,使传统的广场活动与现代舞台艺术得到了完美结合。每个演员充分表达的舞蹈语汇,哪怕是手指的变化,有的夸张到极致,有的细腻到极致,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马蹄的声音,生命中涌动着艺术的张力,在观看时你会感到,原来舞蹈不只是轻歌曼舞、涓涓细流,舞蹈也会有如此大的气魄。那种身体沾染着泥土的淋漓尽致的表演,会让人笑、让人哭,让人相信这里的青草会跳舞,这里的石头会说话,这里的神灵在保佑着你。
《云南映象》实际上唤起了人们对自然越来越多的依恋,民间艺术理应成为现代审美情趣的支撑。在《云南映象》里,我们找到了自己敬畏自然、回归自然的心。“他们 (专业舞蹈演员) 是跳舞的,我们是跳命的。也许他们也信仰舞蹈,但信仰舞蹈和我们从精神上、本质上去信仰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杨丽萍的舞蹈人生所在,正是这一点,促使她把《云南印象》奉献给更多的人。
遗憾与担心
云南的民族舞蹈成为一个品牌可以在各个城市巡演,这是对民间文化的一种保护和弘扬,可以说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而杨丽萍也由原来的舞者成为了一个策划者,这是对她低调宁静个性的一种突破,某种程度上何尝不是一种超越。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
《云南映象》已经连演了一百多场了,还将演下去,而且今后《云南印象》很有可能被改成《走进香格里拉》推到外国去巡演,掌控权或许已经不在最初做这个歌舞集的艺术家手中,民族的东西一旦真的有了只要那么一点点迎合市场的趋向就不再是纯粹民族的东西了。那种欢庆时所有的人一起跳舞尘土飞扬的自在,散场后满地都是鞋子的姿肆,又岂是金碧辉煌的大剧院可以再现的。原始的激情被重复几百次后还有没有最初的张扬和感动?当发自内心的狂欢成为众人观看评说的盛会,还会不会有初见时的淳朴?
而还原《云南映象》的杨丽萍从前说:“我永远都是村子里的人。”她对于舞蹈那种与生俱来的信仰没有变,真正的淳朴蕴涵着大智慧。问及杨丽萍的理想,她只是想回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踏歌起舞的童年生活。离开舞台实际上是回到了她原来的状态,她可以表演给自己看,可以是在家里跳,或者是在河边、在树林里跳,真正回到舞蹈本身。
如今她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昆明,《云南映像》的票房收入超过千万;在浙江,9场演出场场爆满; 在上海,获得了中国舞蹈最高奖项;2004年4月上旬在北京,还未上映早就一票难求,杨和她的歌舞团已经成为媒介的重要目标。一生做成这样的事对杨丽萍是大幸,对民族舞蹈是大幸,可是对她的艺术生涯是纯粹的大幸吗?真正的艺术恰恰是需要适度离开尘嚣获得真正的超越,一个智慧女人的一生也是如此,现在或以后的杨丽萍是否还可以保持最初的笃定与淡然?当看着那些真正从山野出来的舞者穿得一个赛一个时尚,越来越远离生养他们的纯净的苍山洱海的时候,杨丽萍的内心是否也会有一丝丝的遗憾。当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一次次聊天一次次上电视的时候,她内心会不会也感到一丝丝的疲倦。没有人会知道,只有等待时间静静地评判,只有等待精神与心灵的眼睛默默地穿透这一切。
| |
|